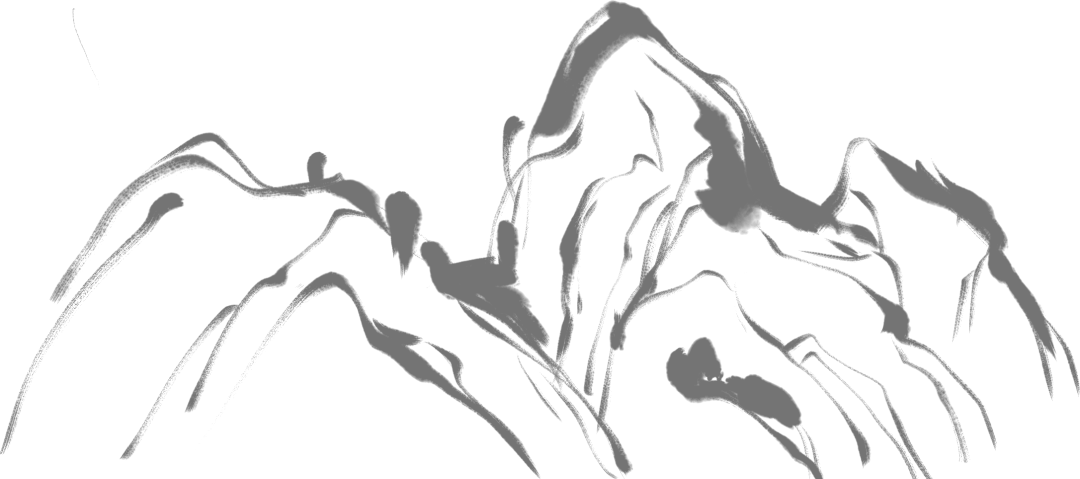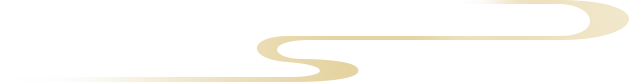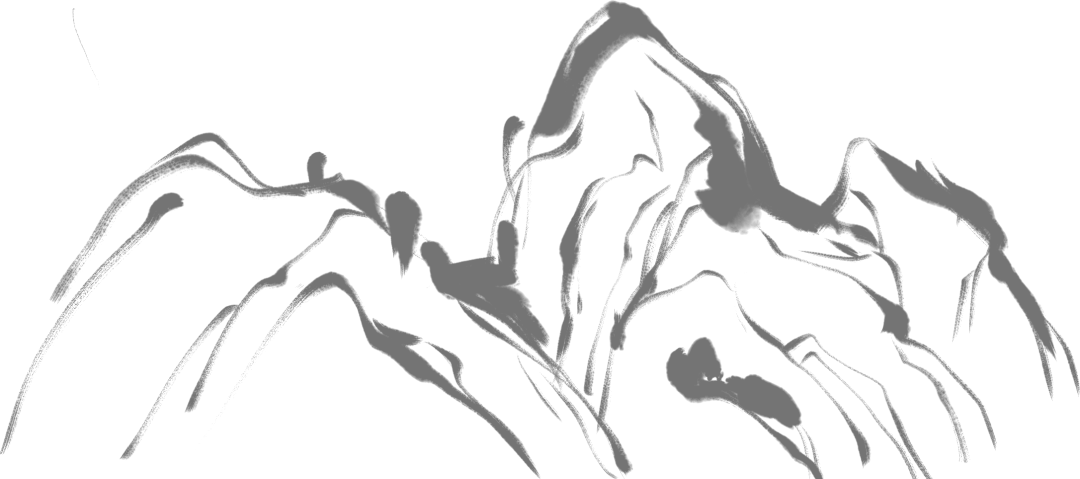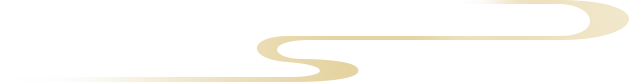屏南寿山初创乱弹之时,已是道光年间。班主苏兆岁聘请闽浙赣三省乱弹名艺人,成立“三省福”乱弹班,在屏南及周边演出,演出过程中不断吸收徽调、汉调、滩簧及民间小调,形成了以西秦腔和吹腔发展起来的“平板”,并以此为基调,另一类是叠牌,旋律平易流畅,还有就是小调曲牌。演艺市场在清末进入鼎盛,足迹遍至闽东古田、寿宁、宁德、福安等地,乃至浙江、江西等外省,老一辈艺人中亦不乏被聘为戏师傅传授技艺的。
当时,福建乱弹在台湾也颇为盛行。据载,“台湾之剧,一曰乱弹,传自江南,故曰正音。”(连横著《台湾通史·风俗志》)至今,台湾民间还流传着一句俗语:“吃肉吃三层,看戏看乱弹。”五花肉肥瘦相间的多层次与乱弹诸声腔的花杂之意,倒是十分“意趣相投”,这也不难看出乱弹在民间的喜闻乐见。
“檀板金嗓歌盛世,寿山福海庆生平”,殊不知,苏氏祠堂的对联还辉映着寿山茶兴曲盛之时的图景。清代五口通商后,寿山茶业进入鼎盛,小小村庄知名茶行就有八处,所产红茶、绿茶远销外洋。遥想当年,身居深山的寿山“货郎”,肩挑背扛行走在通往外界的茶盐古道上,这一头,乱弹的余音还萦绕耳际,货郎就要和月亮一同踏上深邃的山路,货担里满载茶叶、硋瓷、木材、红曲等农产品,行路迢迢到沿海换取盐巴,这个微小而平凡的晶体,在很长的一段历史里,曾让多少人为之狂热地寻找、交易,甚至争夺,而乱弹之于寿山百姓,又何尝不是精神的盐粒?据称,抗战时期,随着战火的蔓延,人丁凋零与生存危机让乱弹的生存空间极度紧缩,戏班相继解体,曾经的鼎盛骤然覆灭,但屏南寿山的乱弹班还在,他们在硝烟里用充满乡愁的曲调,带给了寿山群众坚守的信念。
岁月更迭,老戏演了又演、代代传承,熟悉的乡音和祠堂的香火一同绵延,鲜活地调和着村民们朴素的日常,进而演变成一种风俗,烙印在一个宗族的史册。陈独秀先生有言,戏园者,实普天下之大学堂也;优伶者,实普天下之大教师也。寿山自古崇尚耕读文化,那一个个关于礼义廉耻、善恶美丑、人情冷暖的故事,曾在每一个节庆、农闲之时,一遍遍地唱进寿山百姓心中。
二百年后的寿山乱弹,景况远不复当年。尽管数年前随着“屏南乱弹戏培训基地”、乱弹戏保护传承协会的开设成立,给一度沉寂的寿山乱弹平添了不少活力,但古老剧种的保护传承与发展,从来就是难解之题。
兴之所至,趣之为开。寿山的年轻人还在陆续地走出山外,留在村里的人们也乘着网络的翅膀远眺世界,唯有土墙上斑驳的笔记,祠堂里镇守的先祖与神龛,古道上通往故里的风,默默记取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浓情厚谊、喜笑悲欢。